1968年5月,在法国巴黎爆发了一场特别的运动。虽然它不是暴力革命,但是也有街垒、冲突和流血。它的时间不长,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其影响却贯穿了整个二战之后的法国社会,直到今天,法国乃至欧洲都还必须面对这场运动的精神遗产。巴黎的街垒从筑起到拆除,到今天已经整整四十年,无数思想家都在努力反思,使用
法国社会学家让-皮埃尔・勒・戈夫的著作《1968年5月,无奈的遗产》试图以独特的视角寻找1968年革命及其参加者的精神活动和脉络,并对这场运动在法国战后精神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进行总结。实际上,在这场风暴发生之前,没有人能够预见到它的来临。当时的法国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阿尔及利亚战争已经彻底结束,似乎已经没有人关心政治,民众讨论最多的无非是电视和洗衣机这样能提高生活质量的新发明。然而,风暴就是在一派欣欣向荣的平静气氛中发生了。大学生从对学校教育的抗议开始,从校内走向街头,一系列小规模的冲突不断发展,引发了五月十日拉丁区(巴黎的大学和文化区)的街垒之夜。巴黎道路的一块块铺路石被挖出来,“修筑街垒在示威者中创造了一种兴奋、友爱和节日般的气氛”。然而,当天晚上的镇压是残酷的,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倒在警察的棍棒之下,医院挤满伤员。但是镇压反而激起全体市民的同情,工人参加到学生队伍中,舆论也一边倒地批评政府的野蛮行径。警察退出了拉丁区,庄严的索邦大学被大学生们占领,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对当时的青年学生来说,“自由有理,革命无罪”在一夜之间成为生活的信条。大家聚集在广场,肆无忌惮地表达对一切禁忌的不屑,惟一需要禁止的东西就是“禁止”本身。这是一场狂欢节般的运动,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被打破了。作家索莱尔斯(Sollers)在回忆“五月”的时候说:“在五月,我们做一切让我们开心的事情。城市已经静止,一切都停下来,翻了个个儿。五月给我的印象是巨大的宁静。我们不停说话,不睡觉,我们都在构思最激进的理论,互相攻击,辩论,这些美好的日子既是爆炸又是静止,留下安详的回忆……在斗争之外的是每个人的冒险生活,每个时刻都感受着令人神往的节日。清晨的天空,空旷的街巷,宪兵追来时的奔跑,着火的汽车,偶尔看到的尸体,语句和笑声在陌生人之间快速的流动。”法国知识分子对1968年的怀旧不仅是政治的,也是抒情的和美学的,有某种超现实主义的色彩。但是社会不可能停留在暴力与欢笑之中,政府最终打败了疲惫不堪的学生,恢复了秩序。从六月开始,社会逐渐恢复平静。
这是一次奇特的运动,斗争的双方从各自的角度来说都取得了某种胜利。政府最终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保证了人民的正常生活。然而反对者也绝非没有收获:工人的地位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有所上升,左派力量继续壮大,五月风暴是左派的强心针。二战后的法国知识界向来就被左派占据,五月运动中,左派知识分子纷纷走上街头支持学生,萨特亲自走上街头出售《人民事业报》的镜头直到今天看来依然激动人心。
对1968年的评价总是众说纷纭,甚至索邦大学也因此分裂。革命的支持者与反对者无法在同一个讲台上和平相处,左派的青年教师在凡桑建立巴黎第八大学,而右派的教授们则依然坚持索邦的荣誉和尊严,他们固守的巴黎第四大学继承了索邦的校址和校名。第八大学的教授一般不打领带,第四大学的教授则西服革履,两个学校的教授从外表上就区分开来。
勒・戈夫的著作追踪考察五月运动之后所发生的变化是一个有意思的思路,这从他的书名就可以看出来。书名的原文l’héritage impossible直译过来是“不可能的遗产”,意思是当代法国已经不可能把1968年运动当作一份“遗产”来接受,这个标题就表明了作者的态度。戈夫认为,极左派试图使自己成为1968年运动精神上的继承人,他们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汲取思想资源,认为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可以一劳永逸地创造一个自由解放的世界。几年前,我曾经读过克里斯特瓦颂扬“批林批孔”的文章,看到一个法国知识分子对“文革”的顶礼膜拜,让人感到有一丝无奈和讽刺。在戈夫看来,这些“革命行动”与其说是为了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努力,不如说是一场心灵戏剧,他们以为自己在打碎一个旧社会,建设一个新社会。但是这一切似乎更多是他们的想像,而不是属于人民的现实,如职业政治活动家多莱所说“我把什么都混在一起了:半冒险半革命的汉堡海员、哲学政治学指导员的轻机枪、心地善良的无政府主义妓女、黑格尔锐利的观点和西班牙战争……简而言之,我之所以成为共产党人,是因为我认为过日子的惟一方式是活得像一部小说……这一代年轻的共产党人把历史当作小说……改变生活。4年的闯荡,值啦!”
“另一种活法”是1968年运动最令人激动的渴求。资产阶级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窒息了人民的精神,为了让乌托邦成为现实就必须抛弃现有的文化,因此68一代人(soixante-huitards)在文化领域进行革命,开辟了新战线,一切反面的价值观都被当作革命性的。性解放、吸毒、反家庭、同性恋,一切欲望都是革命,一切对欲望的控制都是反革命。上世纪70年代,对身体欲望的崇拜成为法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青年的信仰,他们企图用自己的身体为武器对社会和文化权威说:不!以自我毁灭作为射向传统的子弹。他们对文化纵情破坏,并体验到精神和身体的双重狂喜。但是这种文化造反也只是一台戏剧,而不是一条出路。英国电影《猜火车》就表现了青年们在反叛中的迷失与痛苦。情绪动荡的阶段之后,《古拉格群岛》的出版和中国“文革”的真实信息传播到法国知识界,引发了对“革命”的置疑,这是对极左派的沉重一击。革命这个概念是否具有绝对的合法性?在法国这样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国家,知识分子开始思考革命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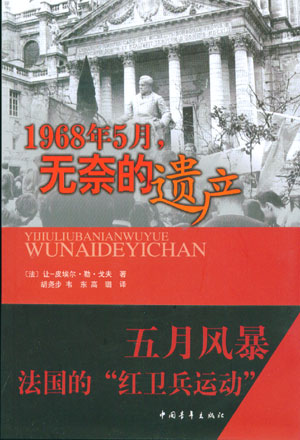 不管怎么说,1968年运动毕竟在法国战后僵硬而缺乏活力的文化堡垒上狠狠踹了一脚,打开了一扇透气的天窗。今日法国的言论自由和人道主义氛围不能说没有五月风暴的功劳,甚至可以说,工人阶级和社会低层享受到的各种福利不仅需要左派的理论武器也需要大学生的理想主义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没有必要把1968年的运动单纯看成破坏或者建设。作为一次破坏性运动,它没有成功,然而,这似乎更加确保了它的正面价值。这看上去是悖论,但也是实情。
不管怎么说,1968年运动毕竟在法国战后僵硬而缺乏活力的文化堡垒上狠狠踹了一脚,打开了一扇透气的天窗。今日法国的言论自由和人道主义氛围不能说没有五月风暴的功劳,甚至可以说,工人阶级和社会低层享受到的各种福利不仅需要左派的理论武器也需要大学生的理想主义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没有必要把1968年的运动单纯看成破坏或者建设。作为一次破坏性运动,它没有成功,然而,这似乎更加确保了它的正面价值。这看上去是悖论,但也是实情。
“1968年5月”在今天几乎变成了一个神话和符号,它不再是一种体验。对于法国人来说,它是乌托邦精神和无政府主义的一次尝试,它是某种情感的回忆,是“为一种思想去死”(Mourir pour une idée)的流行歌曲;对于中国人来说,它发生在四十年前的异国,但又是与中国的精神状态息息相关的一次事件,甚至到今天,对它的反思依然对我们有现实意义。中国的知识界也在通过68运动探索文化的继承与革命的交替运动,研究社会的秩序与变革之间的关系。而更重要的是,寻找我们自己的天窗。
(《1968年5月,无奈的遗产》,让-皮埃尔・勒・戈夫著,胡尧步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4月版,42.00元)
(本文编辑:朱岳)
